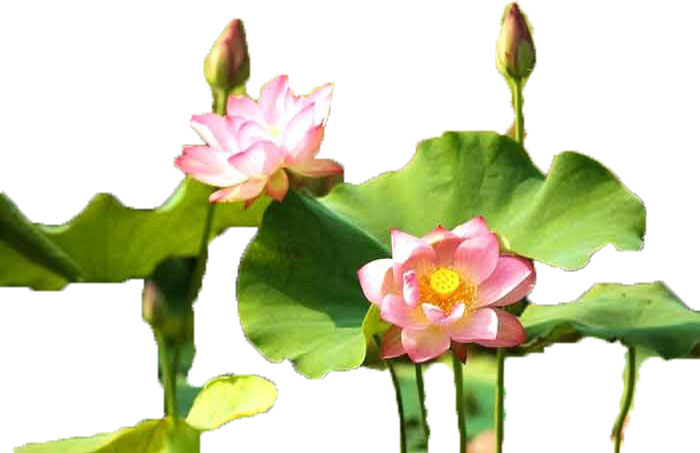信心之力,迷雾中的永恒灯塔
刊发时间:2025-05-05
A3版
作者:陈德荣
20世纪80年代,在云南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里,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竹篓,赶着几头猪在山坡上徘徊,那就是我,一个因不会求“阴影面积”而数学考砸、自作主张退学的五年级学生。面对父亲的竹条和怒吼,我虽被“赶回”教室,心却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,飘荡在课本之外。
命运的转折始于六年级。那年,我没有考上初中,也是那年,大河完小五年制改为六年制。班主任李文俊老师的第一堂课,竟点名让我当学习委员——班里全是落榜生,我的成绩排在班级最前面,我竟成了班里的“佼佼者”。那个瞬间点燃了我蜷缩的自尊。晨读时,我站在讲台前领读的声音格外洪亮;夜晚,煤油灯下反复演算数学题的身影,成了土墙上一幅倔强的剪影。毕业时,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首位。
原来,被信任的力量,足以让荒芜的心田开出花来。
初中的油印试卷像一片片雪花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英语单词与物理公式交织成密网,困住了一群山里娃。学校中考曾经被“剃光头”的传闻,让教室里的叹息声比读书声更响。直到某个午后,班主任宣布:“期末前三名奖励五块钱!”——在五分钱能买颗水果糖的年代,这无异于一座金矿。
我蜷缩在家里的小木楼里复习,月光从瓦缝漏进来,照着张海迪的故事:高位截瘫的姑娘,用收音机自学三门外语。书页上的泪痕未干,期末考卷上已写满密密麻麻的答案。当“陈德荣,鼓励奖五元”响起时,我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冲进供销社。两块钱的水果糖甜得发腻,却让我尝到了比糖更珍贵的滋味:原来拼命踮脚,真的能摸到星光。
初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,我的数学考了全班第一。1994年盛夏,我背上行李走进临沧农校,成为大河中学三名中专生之一。离乡的班车上,我穿着唯一能穿出门的蓝色长裤,裤角边还沾着早上打猪草时沾上的泥星子。
中专毕业,我被分配到大寺乡林业站工作。当同事们为写总结抓耳挠腮时,一场乌龙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某日,宣传干事举着《临沧报》冲进办公室:“陈德荣,你的文章见报了!”报纸上是篇林业报道,作者却是县局同名同姓的老同志。
那晚,煤油灯在窗台上摇曳。我翻出泛黄的作文本,把《临沧报》上的文章剪下来贴在墙上。方格信笺成了新战场,一篇《大寺乡完成造林任务》改了七稿,寄出时信封角都被磨出了毛边。三周后,当油墨香从邮局飘来时,我知道自己打赢了人生最特别的“战役”。
此后十年,从乡镇林业站到市局办公室,从“通讯员”到“特约记者”,上千篇稿件在各级报刊落地生根。2007年《临沧日报》创办二十周年表彰会上,我站在领奖台上,手里“优秀通讯员”证书的重量,竟比当年那包水果糖更沉甸甸。
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,除了写作新闻作品外,我还向“文学高地”进军,通过积极创作,散文及微型小说作品发表《中国文学》(香港)、《中国铁路文艺》等期刊上, 作品被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月报)《绝妙小小说》等刊物转载,作品还入选《中国美文二十一世纪十年精选》等选本,出版个人专籍《苦荞花》,并加入中国散文家协会、临沧作家协会,被市科联聘为社科专家。
2024年秋,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进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场,周围年轻考生惊诧的目光,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个赶猪少年。客观题放榜那夜,查询页面的蓝光映着鬓角白发,鼠标点击声如战鼓擂动——我竟然通过了客观题考试,那时,我忽然想起张海迪书里的话:“轮椅困住我的身体,却困不住我丈量世界的脚步。”如今,我摸着法律条文里密密麻麻的注释,仿佛又看见六年级教室里,李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的那个圆——人生如圆,信心是永不偏移的圆心。
从放猪山坡到法考教室,从方格信笺到获奖证书,信心的年轮在岁月里悄然生长。她教会我:被点燃的信任,能让最卑微的种子冲破岩层;五块钱的甜,藏着改写命运的密码;
同名乌龙,原是命运递来的笔杆;五十岁的考场,证明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。
正如里尔克所言:“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当我在案头写下这些文字时,窗外的攀枝花正开出火红的花朵。那些曾被数学题难哭的夜、为稿费雀跃的晨、翻法条至天明的时光,都化作年轮里最坚硬的木质层。
信心的力量,从来不是瞬间绽放的烟火,而是用岁月打磨出的、永不停歇的光。